當今社會,網絡給人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已經成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它迅速便捷,傳輸量大,自由化程度高,幾乎具有其他一切傳播媒介所沒有的優點。作為一種新生事物,網絡傳播的出現也必然伴隨著社會關系的改變,信息網絡傳播權就是在此情況出現的。作為一種新的財產權利,彌補了原有法律規定在專門調整網絡著作權法律關系上的空白。然而,現有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定義使得其與其他著作財產權有所重疊與遺漏,本文就“信息網絡傳播權”與“廣播權”的重構提出自己的建議。
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重構
“信息網絡傳播權”是我國《著作權法》的用語,按照《著作權法》第10條第12項的規定,是指“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
我國增設信息網絡傳播權,是借鑒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第8條中“向公眾傳播權”。差別在于,條約第8條的最后一句是“包括將作品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的成員可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獲得這些作品”。可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中的“向公眾傳播權”泛指一切“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的行為,“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的成員可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獲得作品”的行為只是其中之一。而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表述,信息網絡傳播權特指“使公眾可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獲得作品”的傳播方式,其含義窄于“向公眾傳播權”。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草案備忘錄第10和第11段的解釋,條約第8條最后一句的目的在于:明確地涵蓋請求式的互動傳播行為。既然我國的立法直接借鑒了條約,備忘錄的解釋有助于我們明了“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含義:特指請求式的互動傳播行為。我國用“信息網絡傳播權”對應“on-demand avail-ability right”,不利于公眾“望文釋義”。根據《辭海》對“信息網”的解釋,信息網泛指信息傳遞和交換的網絡,如情報網、通信網、計算機網等,這個概念遠遠大于“請求式互動傳播”。另外,網絡直播雖然也屬于信息網絡傳播,但是它不滿足使公眾可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獲得作品,所以也不符合“請求式互動傳播”。信息網絡傳播的名稱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中“向公眾傳播權”的其中的請求式的互動傳播行為的含義不符。
筆者認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定義應做以下規定,即將作品或者作品的復制件被置于網絡環境中,使公眾具備獲得作品或者復制件的所有權現實可能性的權利,并且在公眾獲得作品的復制件的所有權的同時,不影響原權利人對作品或者作品的復制件的所有權與其他公眾獲得作品或者作品復制件所有權的可能性。”
對廣播權的規定亟需完善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將規范廣播作品產生的法律關系的權利規定為“廣播權”,是指“以無線方式公開廣播或者傳播作品,以有線傳播或者轉播的方式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以及通過擴音器或者其他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類似工具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的權利。
我國已加入并批準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該條約第8條要求締約國通過國內立法確保“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作者享有專有權,以授權將其作品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包括將其作品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可獲得這些作品”。我國《著作權法》雖然規定了“廣播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這兩項專有權利,但在保護效果上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第8條的要求仍然存在差距。表現在直接通過有線系統和計算機網絡進行的非“交互式”傳播無法受到“廣播權”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保護。
筆者認為,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問題,是因為《著作權法》在規定“廣播權”時完全照搬了《伯爾尼公約》第11條第2款的規定,而完全沒有考慮到《伯爾尼公約》之后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伯爾尼公約》的最后一次修改是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不但沒有互聯網,而且有線電視系統的作用與今天也完全不同。《伯爾尼公約》中的“廣播權”只規范“以有線方式轉播廣播的作品”,而不規范“以有線方式廣播作品”的技術背景。
三十余年來,傳播技術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線電視系統的主要作用,早已不是轉播無線節目,而是直接播放電視節目,同時網絡這一新的“有線”媒介也得到了迅速普及。“廣播權”不應局限于《伯爾尼公約》中的“有線轉播”,而應拓展到以各種技術手段直接通過有線系統傳播作品的行為。可見,《著作權法》對“廣播權”的規定早已過時對其重構也勢在必行。
從廣播的形式分析,在著作權法領域廣播的實質是以能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工具向公眾傳播適于廣播的作品。如果作這樣的理解,網絡傳播也應包括在其中,因為網絡也是能夠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工具。網絡傳播與傳統廣播的區別在于前者可以讓公眾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而后者不能,公眾無法控制廣播節目的播放時間,一旦錯過節目播放時間便無法再接收到。但這種差異,僅僅是技術含量的差異,并無本質區別。根據“技術中立”的立法原則,一種行為的法律定性不應當取決于其借以實施的技術手段,而應當取決于行為自身的特征和后果。而且法律并未明確規定廣播不包括公眾能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傳播形式。因此,將網絡歸入法律規定的“類似工具”無可非議。
因此筆者建議,網絡傳播只要不符合筆者建議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定義,則不應當由信息網絡傳播權來調整,而是交由廣播權來調整。
推薦閱讀
8月15日消息,國內綜合廣告和媒體服務商昌榮傳播近日正式對外宣布,為進一步提升昌榮傳播集團核心競爭力,適應新形勢下的經營戰略發展需要,經董事會研究決定,正式任命陳熹女士為昌榮代理業務總裁,全面負責昌榮傳播>>>詳細閱讀
本文標題:評論:重構信息網絡傳播權與廣播權
地址:http://m.sdlzkt.com/a/05/20120817/81076.html

 網友點評
網友點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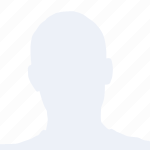
 精彩導讀
精彩導讀



 科技快報
科技快報 品牌展示
品牌展示